山仑:转基因作物育种发展阶段、问题与建议
山仑:转基因作物育种发展阶段、问题与建议
2014-03-26 冷泉港实验室
近年来,转基因品种安全性问题在我国学术界和民众中引起了一些争议,这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不应称之为“妖魔化”,也不拟采取“坚决遏制负面舆论”的做法。毋庸置疑,转基因育种技术将以巨大的潜力引领未来,对于增强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支撑我国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年第3期发表了两篇倡导发展新一代农作物生物育种技术的文章,随后《中国科学报》等报刊陆续有文对此加以论述;一些专家提出的战略咨询报告也用了这一提法。我非育种工作者,读了这些文章后增进了知识,也受到启示,但有一个概念方面的问题,经反复思考后仍不甚明了,现提出来同大家讨论,请专家指教。
生物育种涵盖了从基因工程到杂交选育共七类技术
什么是“生物育种”?从字面上看似可理解为植物、动物、微生物育种的统称。从国家已启动的重大科技专项“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的名称看,这一理解看来是适当的。但《2013-2018年中国生物育种业市场前景分折与投资风险评估报告》则认为“生物育种的定义是培育优良生物的生物学技术”,涵盖了从基因工程到杂交选育共七类技术。
黄大昉先生所赋予的定义则是“农作物生物育种是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融合了分子标记、杂交选育等常规手段的先进技术”,并强调“生物育种又称转基因生物育种”,但“千万不能把生物育种狭隘地理解为只是转基因,它还包括了传统育种的先进技术”。我直观感觉上述列举的定义不够清晰,且相互交错。另外,当前是否已处于建立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育种技术体系的时候也值得商榷。
上面列举的中科院院刊两篇论文的英文摘要中,作者分别将“生物育种”译为“Bio—Breeding”与“Biotechnology Breeding”,前者为中文原义,而我认为后者的含义是适当的,即“生物育种”的确切表达应为“生物技术育种”,或称之为以转基因技术为主导、包含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分子标记等技术在内的生物技术育种,“生物技术”不等同于“生物学技术”,目前不应将常规育种技术(如杂交选育)包括在生物技术育种体系之中,而应倡导两者的紧密结合、协同发展。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要加强分子育种的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我理解,此处所说的“分子育种”与“生物技术育种”含义基本相同,是一种简称,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更强调在分子和基因水平上精准操作的遗传改良。鉴于此,我想将问题引申一下,就常规育种与转基因育种(生物技术育种的核心)之间的关系,以及转基因作物育种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谈谈个人的认识。
转基因作物应服务于我国当前和未来农业发展需求
近年来,转基因品种的安全性问题在我国学术界和民众中引起了一些争议,这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不应称之为“妖魔化”,也不拟采取“坚决遏制负面舆论”的做法。按常识判断,我个人认为,按程序经严格审定的转基因食品和普通食品一样是相对安全的,但其遗传效果和生态效应有待长期观察的主张也是有道理的,故在一个相当时期里应允许人们有选择权。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转基因作物应用不仅有一个安全性问题,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证明其不可替代性,以及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当前和未来农业发展的需求。
毋庸置疑,转基因育种技术将以巨大的潜力引领未来,对于增强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支撑我国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势所趋,非搞不可。但就生产环节而言,当前占主导地位的仍属常规育种技术。据报道,转基因品种种植面积近年来在一些国家有很大发展,如转基因大豆在美国种植率高达90%以上,玉米则达到70%,但仅限于两类基因,抗虫害与抗除草剂(且具特定性);近年来我国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其优势之一是含油量高,但这一性状并非转基因的效果。
可以认为,目前为止,与产量直接有关的基础性状仍是通过常规育种技术获得的;从长远看,转基因技术作用的发挥仍然必须以常规育种作为基础。这里需要强调的另一个问题是,我国作物育种方向长期以来以高产为主,并追求超高产目标,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是必要的,但今后为实现大范围的持续均衡增产还必须重视确立明确的抗逆、广适应育种目标,特别是抗干旱与水土资源高效利用目标。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培育一批突破性新品种的要求,从哪里突破?在什么性状上突破?我认为,主要应从抗逆性上,特别是在改善抗旱节水性状上寻求突破。
对转基因抗旱节水新品种的看法和建议
从原理上看,通过转基因途径培育抗旱节水新品种大有希望,但实际上困难很多。这既是当前的一个研究热点,也是一个难点。据报道,全世界已有数百个干旱响应基因被分离出来,并获得相当数量的转基因植株,但长期停留在实验阶段。经历多年努力,美国孟山都公司于2012年推出第一例商业用抗旱转基因玉米(CSP B Corn),中等干旱条件下平均增产6%,因未显示出其明显优越性,推行并不理想。我国近年在河北、山西、山东、陕西、甘肃等地用常规技术培育出一批小麦、谷子等抗旱性较强的新品种,并得到推广应用。
2005年在罗马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干旱大会的总结中曾指出“基因组研究信息如此之多,但这信息在缺水条件下的田间应用又如此之少”;2013年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干旱大会的通告中再次呼吁,应重视植物抗旱性分子研究与田间应用之间的衔接,为消除它们之间的巨大缺口,应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协调配合。
学术界早已明确,植物抗旱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特性,不但是多基因控制的,而且是通过不同途径实现的,加之当前抗旱转基因研究又多限于机理尚不十分清晰。且与高产性状存在一定矛盾的耐旱性范畴,即通过基因工程能控制的抗旱性状仅是一小部分,而且其表达效果严格受到环境条件的限制,故难度很大。
有学者指出:“不论是抗旱还是抗盐,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真正的转基因抗逆农作物还没有出现,特别是很抗逆的作物,目前还停留在人们的想象中。”基于上述情况,就通过转基因途径培育具有突破性的品种,特别是培育抗旱节水新品种的有关问题,提出几点个人看法和建议:
1.转基因作物育种具有很大潜力,是育种工作取得新突破的希望所在,但不论当前和未来都应强调转基因育种和常规育种的紧密结合,而且以常规育种作为基础。当前不拟笼统倡导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在生产环节上仍应坚持以常规育种技术(包含杂交选育、杂种优势利用、理化诱变等)为主,在研究层面上则应切实加强转基因育种的系统性研究和有针对性开发。
2.在育种目标上,在继续重视高产与超高产性状的同时,应将另一重点放在抗逆与广适应上,特别针对广大旱区和缺水灌区,选育抗旱节水新类型已成为一种迫切需求,这方面虽然面临不少困难(如抗旱机制的复杂性、干旱环境的多变性、可控制性状的局限性等),但转基因技术仍属最终解决这一难题的最佳选择,不过要有耐心,应作好长期努力的思想准备。
3.在研究对象上,除农作物外,将抗旱转基因植物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放在林草植物上更为可行,因为这方面的抗逆基因资源更为丰富,而且与一年生农作物相比,这类植物存活需求是第一位的,产量高低是第二位的,生态效益在先,只要生存下来就有机会实现其生态经济目标。
4.切实加强抗旱转基因育种的基础理论研究,这方面目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近年来植物抗旱机理研究相对分散与滞后,难以适应抗旱转基因技术迅速发展的需求,例如难以为确定耐旱主效基因及耐旱有关基因的有效聚合提供更有力的依据;二是实验室分子水平研究与田间应用之间缺乏有效衔接,或存在较大空白,整体(个体)抗旱生理机制研究一定程度上被忽视,这也削弱了转基因技术的更好发挥。今后应在这方面制定一个有指导作用的系统研究方案。
5.在政策层面上,今后应重视以下几个问题:(1)在科技立项上注意保持常规育种和转基因育种之间的平衡(包括人才培养、资金投入、条件建设等);(2)对转基因育种除安全性外,应重视全面评价其实践效果;(3)重视不同学科专家之间的协同、交流及相互质疑,例如有关重大项目的立项、评议等活动除本学科专家外,应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参与,鼓励开展争议,以求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取得共识。
作者简介:
山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中科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评论列表 共有 0 条评论
最新导读

热门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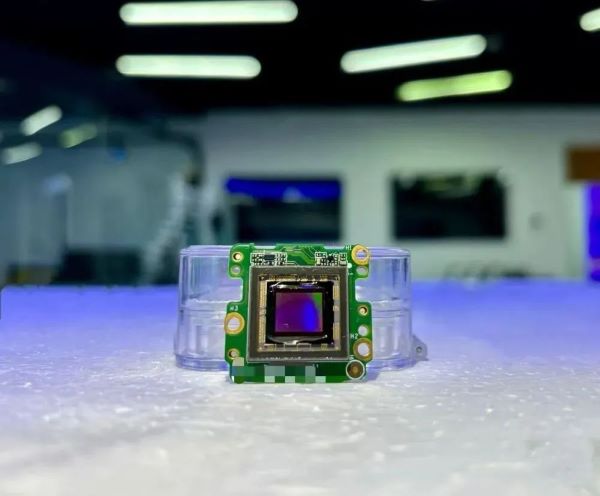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