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飘过半个世纪(雅铮)
歌声飘过半个世纪
雅铮

上世纪中叶,仰光广东大街南北两侧,是闽粤两省籍华侨的聚居地。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十八条街度过的,十八条街的上段多为广东人居住,下段则以闽南人为众。左邻右舍分别是“老再成”饼店和“南安公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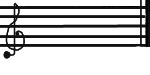
 我家住三楼,进出门需要经过楼底下他人的房间和厅堂,楼梯暗得“伸手不见五指”,成了我们小孩对外界联系的天然屏障。平时都是乖乖地待在家里,和弟妹们共同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看连环画、阅读各种国内期刊、画画、唱歌……。我家常常用电子管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五六十年代播送的歌曲我们都很熟悉,我和弟弟除了会哼唱耳熟能详的曲子外,有时还会拿着歌曲集,学唱各种民族风格的国内歌曲。
我家住三楼,进出门需要经过楼底下他人的房间和厅堂,楼梯暗得“伸手不见五指”,成了我们小孩对外界联系的天然屏障。平时都是乖乖地待在家里,和弟妹们共同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看连环画、阅读各种国内期刊、画画、唱歌……。我家常常用电子管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五六十年代播送的歌曲我们都很熟悉,我和弟弟除了会哼唱耳熟能详的曲子外,有时还会拿着歌曲集,学唱各种民族风格的国内歌曲。
记得小时候,卖酱油车来售货时,都会用车载高音喇叭播放三四十年代的华文流行曲,其中《桃花江》似乎成了它的标志性音乐,当然也少不了金嗓子周璇的歌曲。每当“靡靡之音”响起的时候,就知道酱油车到了,购买各种酱料的人们随之蜂拥而至,争相选购。
每逢春节,不论红白,亲大陆或亲台湾,很多缅华社团都组织贺年文艺队,到各个华区,向侨领和重要人物拜年。新中国刚成立,国民党在仰光的势力尚存。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原国民党少校,每年春节都有军人打扮的管乐队在他住所的马路上拜年演出,演奏短小精悍的军乐,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女军人吹奏的,一种很高亢、亮丽、激昂的乐声,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玩意儿?那个时候我还太小,对西洋木管乐器和铜管乐器知之甚少,感到很新奇,当然后来就知道那叫短笛。伊江合唱团、海燕歌咏团、巨轮社等爱国文艺团体,表演的贺年节目真是异彩纷呈、琳琅满目。小时候我最爱看的是歌舞表演《采茶扑蝶》,在活泼欢快的闽南民歌伴奏下,几个扮演采茶姑娘的演员,一边采茶一边追逐由一位男演员操纵的蝴蝶,蝴蝶模型扎在竹篾顶端,抖抖竹篾,蝴蝶就会活灵活现地飞舞,浓浓的乡音乡情,倍受闽南街区欢迎。
恰逢华人传统节日或民间信仰的祭奠活动,有些缅华社团会在唐人街区里搭台唱戏。在我们这条街,就搭台表演过南管戏、高甲戏、歌仔戏(台湾戏仔)……,这些古装戏我们孩子们来说实在太高深太难懂了,没能留下更多的记忆。而母亲平时用闽南语哼的小调,至今记忆犹新。歌词大意是:正月里来,人博铰(赌博),……矮奴(倭寇)害咱一家散了了……不杀矮奴心不消……。大概是民谣诉说式的“杂碎仔调”吧,母亲早年在鼓浪屿做小本买卖勉强度日,还得养育两个女儿,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痛恨有加。父亲对三、四十年代的革命歌曲情有独钟,由于工作忙,他跟我们交流的机会不是很多,在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聂耳的很多歌他都会唱,最让我感到兴奋的是《大路歌》中“哼呀咳嗬咳,咳嗬咳……”,当时就纳闷,这怎么也算是首歌呢?长大后才知道,它的艺术含量还是很高的。
入夜时分,万籁俱寂,朦胧中传来一位早年丧偶华侨老妇的歌声——《五更鼓》,从“一更更鼓月照山,牵君仔的手摸心肝……”,唱到“五更更鼓天要光,俺厝仔父母叫吃饭……”,曲调即古曲《孟姜女哭长城》,委婉凄凉,老妇时而自创歌词,将不幸身世融入其中,让人深感同情。她唱着唱着声音越来越弱,我们也跟着进入了梦乡。
六十年代初,中缅签订了边界条约,胞波友谊发展迅速,大量的中国电影进入缅甸,那时国内拍的所有影片基本上全都能看到。首都、模范、国泰等电影院几乎成了国产片和港台片的专业影院。每当一部优秀的国产片上映后,影片中的插曲很快就在我们唐人区和华侨学校中传唱开来。如,《冰山上的来客》的“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故乡,当我离开它的时候,好象那哈密瓜断了瓜秧……”;《五朵金花》的“大理三月好风光……”;《刘三姐》的“嘿……什么水面打跟斗,嘿了了啰……”;《花儿朵朵向太阳》的“你看那万里东风浩浩荡荡……”等等,不胜枚举。我家对面的邻居,买了一台盘带式录音机,这在当时绝对是奢侈品,只要他在家就常常播放这些电影插曲,拿现代语言来说,算得上是“追星粉丝”和“发烧友”啦。
过去由于家里并不宽裕,我没多余的零花钱,想学一样乐器,无奈只好选择价格相对便宜的竹笛。买来有关笛子的书籍,完全靠自学吹奏笛子独奏曲。隔壁住着尤氏兄弟,他俩会拉二胡,《光明行》是常拉的曲目,演奏技巧很好。笛声和二胡声交融在一起,如同民乐队隔墙演奏。自娱自乐,真是其乐无穷!
半个世纪过去了,时光如过眼云烟,歌声却还在耳边萦绕。
评论列表 共有 6 条评论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
最新导读

热门文章
















那歌聲,已是一後歷史!
那个年代,唐人街区的歌声、乐声、呼声、叫卖声,多么美妙的交响曲啊,令人难以释怀!
让我回忆起美丽的童年……清晨雾朦胧,小贩叫卖声,还有早起的阿姨们在公用水龙头旁洗衣服棒打的声音,那可怜寡妇杀鸡的惨叫声……
傍晚似乎又听到了她老人家的《五更鼓》,还有她女儿用闽南话唱的采茶扑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