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台南人,我为什么成了统派?
来源:底线思维
文/吕正惠
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生长在台湾嘉南平原靠海边的一个非常小的农村,按行政区划,是台湾省嘉义县太保乡(现在的太保市)的一个小村子,因为村子太小,必须跟邻近的另一个小村子合并成一个行政村。我们村子没什么文化,我小时候的印象,全村没有人讲日语,虽然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为本岛人设立了公学校,但全村好像没人到公学校读过书,因为村子的人非常穷苦,不可能想到要读书。在我的印象里,村子好像也没有设过私塾,可以让小孩读一些最简单的《三字经》和《百家姓》,所以我小时候也没有看过任何汉文书籍。
没想到后来我会从这个村子搬出来,先搬到嘉义市,再搬到台北市,并且接受了国民党政府最完整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最后我居然拿到了中文系的博士学位,成为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后来还当过系主任,在1980年代台独派日渐崛起以后,毅然决然的加入当时台湾唯一的统派组织“中国统一联盟”(1992年)。
我的经历让很多人深感意外,甚至许多中国统一联盟的盟友都不太能理解,我这么一个地地道道的台湾南部人,闽南话讲得好,国语(普通话)讲得结结巴巴,竟然会这么坚定的认同中国。有一次参加宴会,同桌有一位同乡突然问我,“吕教授,你不是跟我一样是嘉义人吗?”我说,“是啊”,“那你怎么会说你是中国人呢?”我有一个学生毕业多年后见到面,也跟我说,我们老板说,“吕老师明明是台湾南部人,怎么会是统派呢?”在那个统独分裂的关键时期,常常会出现这么荒谬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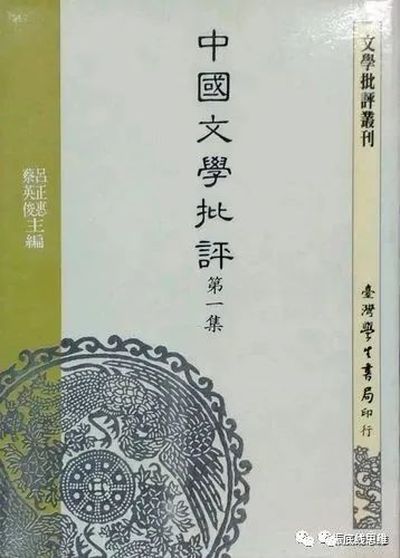
1960年我们家终于在台北市最老的城区万华落户,当年我才十二岁,我父亲可以说是台湾最早的城市打工仔。我父亲的故事值得一讲,我以后也许会为他写一本书。我从小学六年级起就在台北读书,比起乡下小孩,我算是有比较好的教育环境。因为我父亲的个性,我们家一直过着穷苦的日子。跟一般小孩不一样,我从小就很喜欢读书,不怎么跟小朋友一起玩,只要有书读,我什么事都不计较。班上也有一些较有钱的同学,但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同学间的贫富差距。
上了初中以后,我特别喜欢读地理和历史课本,老师还没教到,我自己就先读了。我们的地理课本是一省一省讲,因为按国民党的行政区划,中国有三十五省,每省有一幅地图,读每一省时,我就会把这一幅全省地图摊在窗玻璃上,用一张白纸照描一遍,包括主要的河流和城市。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从初中开始,我就对中国的山川非常熟悉。
我对中国的感情,是透过一省一省的地图描绘出来的。对于中国历史,则是经由背诵每一个朝代,一代一代连接起来的。还不到初中三年级,我就会背诵“唐虞夏商周,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别人读历史,常常会不记得卫青、霍去病、岳飞、文天祥是哪一个朝代的人,对我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考历史时,我从来不会把任何历史人物的时代搞错。
我并不是只喜欢地理和历史,但是这两个科目从小就让我牢牢记住,我是中国人,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有广大的版图,包含三十五个省,十二个院辖市(这也是国民党的行政区划),还有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四大河流。自小学开始,我就和中国的历史和地理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很多人小学一读完,历史地理基本就忘光了,但我跟他们完全不同。
但是,我从初中地理、历史课本所学到的“中国”,却存在着一个重大问题。这个中国,现在却只“剩下”台湾省(再加上福建省的“金门县”和“连江县”),其余的只能算“匪区”,正被“共匪”窃据着,等待我们去“拯救”和“光复”。老实讲,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很难真正理解我们在台湾的中国人的处境。
我只记得,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每年每到一个时候,报纸上都会喧腾着一个话题──又到了联合国表决“中国问题”的时候了(因为我住在台北,我才知道有这个问题,如果我一直住乡下,也许我根本就没感觉)。对于这个问题,当时才十几岁的我,也是无法真正理解的。从初中二年级,一直到大学毕业,整整“熬”过十年以后,才终于“熬”到一个我勉强可以理解的结局──联合国里的中国席位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丧失了中国的代表权。老实讲,现在绝大部分的台湾民众,都还无法理解1971年联合国这一次极为重大的表决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但是,我当时就了解了。
1971年我已读完中文系本科,以我对中国历史熟悉的程度,我已经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正统”之争。国民党说,共产党虽然占据了整个中国大陆,但他们只是“匪帮”,国民政府才是中国正统,虽然现在退守台湾,还是有资格代表中国。但现在,经过联合国每年一次的反复投票,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会员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资格代表中国。
1971年的决议,说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已经完全改变了。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时,“中华民国”自然就丧失了代表权。按照中国历史的正统观念,虽然国民党还统治着台湾,但从法理上来说,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国,台湾人民当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当时我已完全了解这个决议的真正意义。
1971年的决议通过不久,有一天晚上我作了一个“噩梦”,我梦见满山遍野的红旗飘扬在台湾岛上。在此之前,国民党一直宣传,“共匪的统治是多么残暴”,这个“噩梦”表现了我潜意识中对共产党统治台湾所具有的“恐惧感”。我知道这只是个噩梦,是国民党长期恶意的宣传所造成的。一个统治中国全部大陆领土已超过二十年的政权,怎么可能是“非法”的呢?我的理智是这样告诉我的。
一方面感情上对共产党还残存着恐惧感,另一方面又知道共产党统治有其合法性,我必须解决这个矛盾。从1971年到1992年(这一年我加入中国统一联盟,成为公开的统派)这二十多年期间,我内心存在不为人知的心理挣扎,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然我怎么作一个中国人?
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解决。因为我不只对中国古代史有兴趣,同时我也极为关切中国现代史。我高中读的是建国中学,建国中学的隔壁就是牯岭街旧书摊,我常到那里买旧书。那时候有一本杂志叫《传记文学》,每期都会刊载国民党重要人物,如西北军将领刘汝明、蒋介石文胆陶希圣等人的回忆录。过期杂志便宜得多,我不知道买了多少。透过《传记文学》及其他一些杂书,我高中时代已累积了许多的现代史知识,这些知识和国民党教给我的现代史并不完全相合,日子久了,我也会怀疑国民党告诉我的那些历史。到了1971年这个关键时刻,我从读过期杂志和旧书所累积的历史知识就开始发挥重大的作用。
从此以后,我就有意识的对比各种书中有关国、共两党充满矛盾的各种叙述。最关键的时刻是从孙中山的“容共”政策到蒋介石的“清党”,真是异说纷云,让人无所适从。当时国民党官方出了一本《从容共到清党》的“名著”,我一再的翻阅,就是无法理清头绪,连基本的是非都无法判断。现在再加上1971年联合国所通过的有关中国代表权的决议,我终于知道:必须弄清楚国、共关系,必须对“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谁能代表中国,有一个是非判断,才能确定“我是中国人”这一句话的真正意义。
1971年到1983年我从硕士读到博士,研究对象都是唐诗,但我主要的业余精力却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是否应该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答案如果是肯定的,那我只能抛弃“中华民国”。这十几年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没有任何一个朋友了解我内心在想什么。
因为在当时,这是一个攸关生死的问题。在1987年国民党解除戒严令之前,如果你敢于宣称你认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你就是“叛乱犯”了,至少要抓到绿岛关十年,严重的话还会被判死刑。
譬如,就在1971年,成功大学破获了一个“共产党案”,因为有一群大学生组织了读书会,“研究”毛泽东思想。他们买了叶青──即任卓宣的《毛泽东思想批判》,只阅读书中大量引述的毛泽东的文字,而完全不理叶青所写的“批判”。其中的主犯吴荣元(现任台湾劳动党主席,是著名的统派)最初被判死刑,后来改判无期,最后减刑释放。1977年,还有一个“台湾人民解放阵线”案,从案名就可以知道也是亲共的。这一次因为蒋经国下令缩小打击范围,只有三个人被判重刑,后来也都减刑出狱。
我加入中国统一联盟后,先后认识了这两群人中的几个。我跟他们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是一群人,彼此交换读物,而且有了初步的组织,对大陆的社会主义相当向往。我是一个人默默读书,默默思考,而且考虑的主要是中国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前途,虽然读过一些国、共斗争时的书籍,但对共产党还没有深入的理解,那时候我主要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信徒。我加入中国统一联盟后,认识了不少1950年代被捕的中共地下党人,才开始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的革命为什么会走上社会主义这条路?”

中国统一联盟游行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生性内向,只喜欢读书,不善于交朋友。如果我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人,也许就会卷入“成大共产党案”、“台湾人民解放阵线案”及其他类似的小团体,最后被判刑,无法完成学业。我家一直非常贫困,我又是独子(因为父亲一辈子好赌,我知道将来全家的生计只能靠我),因此我全心全意的读自己的书,不参加活动。我就这样读到博士,找到大学教职,并且在研究上得到学界初步的肯定。
因为有了这些条件,解严之后我加入中国统一联盟,就没有了政治上的危险性(起码已经没有叛乱犯了)。在统一联盟的盟员中,属于“成大共产党案”、“台湾人民解放阵线案”的人,或者和我同一个世代(如成大共产党案),或者比我小几岁(如人民解放阵线案)。和他们比起来,我是比较特殊的,我已经有了学术地位,有了不错的专职,而那两案的涉案者根本就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坐牢出来后都要为生活奔波,比我辛苦多了。我比他们幸运得多。
我因为太喜欢读书,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我对中国的认同感自然就形成了。1971年之后,我只是把认同对象从“中华民国”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已。我绝对不可能是独派,也不可能再继续认同国民党这个政权,这样我自然就成为统派。这样的认同过程,和“成大共产党案”和“台湾人民解放阵线案”的朋友是有区别的。他们一开始就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我并不是这样。我是从读书出发,认同中国的历史文化,再从这里,进一步认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认为,一个人认同中国的历史文化,而不认同已经存在了近三十年的人民共和国,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有些台湾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相信国民党教给他们的才是真正的中国历史文化。这样就会造成一个非常怪异的结果:他们相信中国的历史文化,而不认同现在统治整个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认为,这种“文化中国派”是一个更大的矛盾,它已经脱离了整个中国大陆,而只存在于想象的虚空中。我不可能接受这种想法。我是经过二十年的阅读和思考,才完全落实我的政治认同,这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认同道路。
1992年我加入中国统一联盟的时候,刚从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事实上这是一种“表态”,表示从此以后我决心当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加入统盟只是“开始”,此后我还需要走一段更长远的路。这只是探索的开始,我必须把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才能真正了解“我是中国人”的深刻意涵。
其实早在1989年7月初我就第一次到大陆了,那时候我急切的想要踏上这块土地,我不知道我的祖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就当时的情境而言)。当飞机的轮子接触到北京首都机场的地面时,我内心无比激动,因为要不是蒋经国在1987年宣布开放两岸可以探亲,我还以为我这辈子不可能踏上我从小就在地理、历史课本上非常熟悉的这一块大地。
此后,我每年都要到大陆去,刚开始是一年一次,后来次数逐渐增加,有时候多达四、五次。我尽可能的把握一切机会──1995年我当选中国统一联盟主席,担任两年,此后我就有机会带领台湾的大学生和中学老师到大陆各地参观访问,有时候也利用两岸开学术会议之便,到我最想去的地方。
举例来说,单单云南省我就去了四次,最远到达中缅边境的腾冲,黑龙江省我也去了至少四次,最偏远的农垦局(即以前的北大荒)就去了两次,新疆去过两次,还到达中哈边境的喀纳斯湖,最后还去了最南边的海南省。中国所有的省区(包括自治区),除了西藏,我全去过。当然,很多时候是搭飞机,连走马观花都说不上,远比不上古人所谓的行万里路,但至少暂时满足了我“走遍祖国大地”的初心。
我生长在中国东南海边的台湾省,却能够游历这么多地方,让我对祖国的山川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这是我初中时代在窗玻璃上描绘中国地图时做梦也想不到的。我终于有机会从课本上的中国走出来,走进那个苍茫广阔的大地,那个从小就念兹在兹的中国。

吕正惠老师
这只是地理空间上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我把在大陆各地的亲身经历,和书上所学习到的中国历史相互印证。当我到过的地方越来越多,我对中国各地语言和习俗的差异之大,感到非常惊讶。我知道自秦汉以后,中国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但如果就各地的差异来看,这哪里算得是“大一统”?那不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千米都生活在同一种模式之下的大一统,那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形容为“多元”而“一体”的大一统。
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对此完全误解。他们以为,“大一统”是铁板一块,是长期的专制统治人为地造成的,是“不民主”的极致表现。这是从来没有在中国各地生活过的人,“想象”出来的“专制”国家和“专制”文明,这根本和中国的现实毫无关系。
所以,就中国的历史而言,与其说中国境内所有的少数民族最后都被“汉化”了,不如说中国文化是境内所有民族共同融合、塑造出来的。就以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来说,所谓的“汉族”根本就是融合的产物,不然它的人口数不可能会这么庞大。
秦汉以前暂且不论,就从“五胡乱华”开始说起。所谓的五胡,包括匈奴、鲜卑、羯、氐、羌,在隋唐时代中国再一次进入大一统以后,这些民族的后裔基本上都融入了汉族之中。在这之后进入中原地区的契丹人和(金朝的)女真人也是如此(这里也暂且不说元、明、清三代的变化)。在这个时候,我们能说“汉族”是个血统上的民族吗?因此,我们不能顽固的抱持国民党自以为是的正统史观。因为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再加上我又到过少数民族众多的云南、东北、新疆、青海各地,我终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从来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近代西方特别强调的“民族国家观”,认为一个民族应该建立一个国家,或者反过来说,一个国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这样的理论根本不合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因为,中华文明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华大地上所有的民族是可以融合在一起、发展成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我们的历史经验就是如此,所以我们会形成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大一统国家。相反的,整个欧洲的面积也就和中国差不多,但自从近代欧洲各个国家形成之后,各国之间的战争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最后终于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这种惨不忍睹的局面。
作为一个台湾的统派,我在四十岁以后终于能够跨越过海峡,走进中国大陆的各个地区。我所走过的、我所看到的、我所重新学习的,让我的中国观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关于世界文明的知识结构也随之而大为改变。我四十岁以后的生活远比我的前半生要丰富得多,我相信随着中国文明的不断发展,我的生命也会越来越充实,并将在未来十多年内达到我人生的最高峰。
2022年9月1日
【本文转载自“马振衣的书房”,原题为“我为什么是一个统派”。】
评论列表 共有 0 条评论
最新导读

热门文章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