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们”:缅甸乡村的社会关系构建

在“我们”与“空无”之间,根本没有自我得以容身的处所。而如果,在最后,我选择“我们”(us)的话,虽然这个“我们”也只不过是一种表象的雷同,我还是投入其中……我在这个表象雷同与空无(nothing)之间只能做一项选择。
这是列维-斯特劳斯在拜访了一座缅甸乡村佛寺(1950年9月)之后引发的忧思,在我看来,他牵引出了缅甸佛教信众精神世界中最深刻的焦虑与困境,即那些崇尚自我、不依附于他人的个体该如何群居?他们该如何适应一种“我们(社会共同体)”的生活方式?这一问题的本质是对社会何以可能的叩问。然而这种焦虑与困境只是理念层面的,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因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从来不提出问题,他们只是将他们的日常生活呈现在我们面前,然后让我们去思考他们解决焦虑和困境的方式是什么。而构建一种“强礼仪与弱依附”的社会结构就是缅甸佛教信众给列维-斯特劳斯做出的回应,在这一结构中,像原子一样的“自我”构建了一个高度有序的“我们”,并同时在高度有序的“我们”中找到了“自我”的现实方式。所以,问题不在于这是一个等级社会还是平行社会,也不在于这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还是个人主义社会,而在于两个看似对立的社会面向是如何调适的,“我”与“我们”是如何共处的。
一 弱依附社会中的“我们”构建
在纯粹的佛教世界中,只有追求解脱的个体,而否决了人的各种社会角色。但在现实生活中,人需要扮演多重身份以及多重社会角色,需要处理各种“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佛教倡导人们出世,但人的生活恰恰是世间性的。在缅甸乡村社会中,缺乏依附关系的个人如何构建公共生活及其意义便成为了社会维系的首要问题。在前文的相关章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缅甸乡村社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即建立一整套礼仪规范来明确社会成员在村落公共生活中的身份和角色,并强调公共生活中社会成员之间严格的等级关系,要求每个人都各安其位,各尽其职。
所以,我们可以将缅甸乡村社会中的公共生活视为关于身份和等级的社会戏剧,而戏剧表演的规则是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礼仪规范。 由此,松散的、原子式的个人在公共生活中变成了集体人、社会人、 阶序人。为了确保“演员”都能入戏,社会对失礼者和无礼者制定了相应的惩处措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缅人将社会(law:ka)和责任(wut)两个词拼在一起组成礼仪(law:k-wut),这一构词法想要表达的是,人与人缺乏依附关系的背景下,民众依靠礼仪来构建社会、公共生活以及关于“我们”的共同体,“懂礼”和“行礼”由此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社会职责。

乔迁仪式中,吴通稳的岳父、岳母位于最前列,最先进入新居
欧文•戈夫曼区分了社会剧场中两种不同的表演者,一种是“虔信者”(sincere),他们相信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另一种是“玩世不恭者”(cynical),他们并不相信自己的表演,并且不在乎观众是否相信他们的表演。在缅甸乡村社会中,如果要建构有序的、充满意义的公共生活,就需要社会成员在展示身份与等级的戏剧中充当虔信者,而不是玩世不恭者。换而言之,社会剧场需要社会成员充当入戏者,而不是随时出戏的拙劣演员。在社会剧场上入戏,是“我”与“我们”共处的重要精神。
在缅甸乡村,人们从幼年时期就开始学习如何入戏,我们甚至可以将他们的社会化过程视为学习入戏的过程,他们被告知几乎所有的公共生活都是仪式性的,都有相关的礼仪伴随其中,公共生活预设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位置、角色、身份,以及表演的方式,所以人人都要学会入戏,学会做舞台上的虔信者,以使自己的表演能够满足他人的预期,社会秩序正是由此而产生。也许,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不相信等级的存在,以及社会身份的不可逾越,但是,他们需要通过“共情” 将身份和等级在公共生活中表演出来,由此来实现“我们”共同体的构建。在等级戏剧中,社会成员所表演的身份、等级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成员在表演过程中获得了各自在社会中的位置,这种位置的获得使松散的个人转化为“我们”中的一员。

双休日,抱村儿童来到抱寺学习佛经
然而,更深层次的问题仍旧存在,崇尚个人主义、拒绝依附于他人的个体为何愿意加入这场毫无个人主义色彩的戏剧,并在戏剧中充当一个守规矩的、被固化在某一社会等级上的虔信者?也许涂尔干关于社会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的相关表述可以用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般来说,社会只要凭借着它凌驾于人们之上的那种权力,就必然会在人们心中激起神圣的感觉,这是不成冋题的;因为社会之于社会成员,就如同神之于它的崇拜者……它(社会)将我们本身的兴趣置之不顾,而要求我们自甘做它的仆人……正因为如此,我们每时每刻都被迫屈从于那些行为和思想的准则,而这些准则,既不是我们所制定的,也不是我们所渴望的,有时候甚至违逆了我们最基本的倾向与天性。
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对于个体具有天然的神圣性和强迫力,而个体则是社会的崇拜者和仆人,他们有天然的使命去维系社会以及开展群体性的生活。只是,关于社会的思想和准则因文化而异,构建出的社会样态也各不相同。这正是缅甸乡村社会中的那些崇尚个人主义、 拒绝依附于他人的个体愿意来到社会剧场的前台、构建“我们”共同体的原因所在。
二 强礼仪社会中的“自我”实现
在上文中,我们分析了构建、维系缅甸乡村社会秩序与公共生活的方式与手段,其最核心的方式和手段就是强化礼仪规范,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各安其位,各尽其职。然而,在这样一个看起来社会阶层固化、等级森严、高度有序的社会中,“自我”又是如何实现的呢?换而言之,在强礼仪社会中,个人主义的社会空间何在?
欧文•戈夫曼将社会剧场区分为“前台”和“后台”两个相互独立的空间,在前台,人们往往极力表现出能给他人造成良好形象的一面,而有损形象的一面却被竭力抑制和掩盖,在后台,在帷幕之后的区域,那些被掩盖的事实则会得到凸显。在缅甸乡村社会中,我们不能认为“强礼仪”的一面就是缅人想极力展示的一面,而“弱依附”的一面也并非缅人想竭力掩盖的一面,但是“前台”与“后台”的概念对于这一议题仍旧具有解释力。缅甸乡村社会中的强礼仪、高度有序的一面在社会剧场的前台上演,而弱依附、个人主义的一面则是在社会剧场的后台展开。在此,我们可以将前台理解为社会公共领域,,而将后台理解为私人领域。

作者在抱寺举行剃度仪式,左一、左二为其养父母吴明生夫妇
在上述理念的观照下,如何在一个强礼仪社会中实现自我的问题就可以获得一种解释。“自我”与“我们”能够实现共处共生,正是得益于缅甸乡村社会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明晰、相互独立。前台上的表演规则、权力关系没有渗入后台,而后台正是滋生个人主义的土壤所在。在前台,每个人都有积极入戏、彬彬有礼的职责和义务,在后台,每个人都有维护一个只属于自我的世界的权利。而在人与人的相处中,恪守“公私分明”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原则。坚守前台与后台之间的帷幕,正是缅甸乡村解决社会整合与自我实现之间的矛盾的关键所在。
缅甸佛教为民众提供了先验的自我观念,并成为缅甸乡村社会中个人主义的理念基础。但与此同时,佛教式的公共生活也为社会整合做出了贡献。在建构强礼仪社会与弱依附社会的过程中,佛教既是社会整合的向心力,也是自我实现的驱动力,它既促使社会成员集聚于社会的公共生活中,也告诫个人要自己主宰自己的世界,为自己而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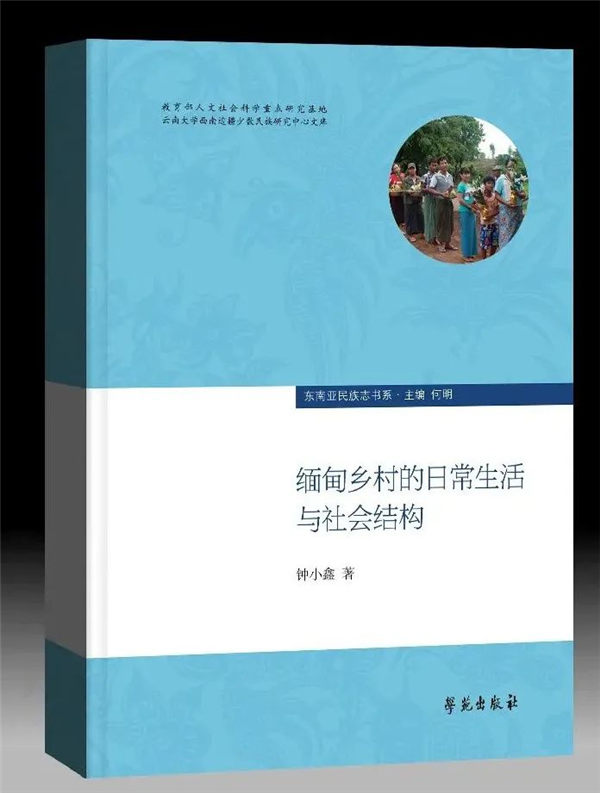
“东南亚民族志丛书” 《缅甸乡村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结构》 钟小鑫著
作者通过在缅甸曼德勒省彬乌伦县的一个缅人村落——抱村的长期田野调查,对村落中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如僧俗关系、亲属制度、年龄结构、性别文化、权力运行方式、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进行了全面的观察和思考。在此基础上,对缅甸乡村社会结构进行了概念界定以及总体性特征的探讨,提出“强仪社会”与“弱依附社会”的概念来描述缅甸乡村社会结构的两个重要面向。
缅甸乡村社会结构在一定程上孕育了当今缅甸政治转型的形式与内容,而政治转型也对乡村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本书认为,当今缅甸激烈的宗教冲突与缅族民众“僧俗共同体”的理想密切相关,持久的族群分化与缅族民众的“族群等级”观念相辅相成,而“僧俗共同体”的理想与“族群等级”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缅甸乡村社会结构所衍生的产物。通过“弱依附社会”的视角,反思了“庇护政治”这一理论范式在缅甸乡村社会中极为有限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关键词 >> 东南亚民族志丛书,缅甸乡村,田野调查
评论列表 共有 0 条评论
最新导读

热门文章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