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我当了五年的“姐姐(周紫依)
那个我当了五年的“姐姐”
新世纪国际中文学校九(1)班 周紫依
记忆的橱柜里,有些往事蒙着灰,有些却总被时光擦拭得锃亮。那件关于属羊的误会,便是其中最令我忍俊不禁又面红耳赤的一件,每每想起,八岁那年的夏日阳光仿佛又热辣辣地照在脸上。
那是我刚搬进外婆家小镇的夏天。八岁的我,在爬满瓜藤的篱笆边,结识了第一个朋友——小莹。她眼睛弯弯的,说话声音细细的,像田埂上怯生生的雏菊。我们迅速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一起在溪边找光滑的鹅卵石,一起在晒谷场上追着蜻蜓疯跑。

一天午后,我们照例相约去田里摘狗尾巴草。走在被太阳晒得发软的泥路上,我忽然想到一个严肃的问题:我还不完全了解我的新朋友呢。“小莹,”我侧过头,很正式地问,“你属什么的呀?”“我属羊呀!”她晃了晃脑袋,辫梢上的红头绳一闪一闪。“真巧!我也属羊!”我高兴地几乎跳起来,一种“我们是一伙的”亲密感油然而生。紧接着,一个更“成熟”的问题脱口而出:“那你几月的呢?”
“我四月的!”她答得干脆。
四月的羊?我心里迅速盘算起来。我生于九月,九比四大,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于是,一种“重大发现”带来的责任感笼罩了我,我挺起小小的胸脯,郑重宣布:“我九月的!我比你大五个月呢!以后,我就是你姐姐啦!”
小莹眨巴着大眼睛,看着我笃定的样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从那天起,一种奇妙的秩序建立了。爬树时,我会抢先说“姐姐先试试这树枝结不结实”;分糖果时,我会把大一点的留给她,并配上“姐姐让着妹妹”的解说;就连闹了别扭,我都会以一种“姐姐不跟你一般见识”的姿态先转身。她呢,也便自然而然地跟在我身后,“姐姐、姐姐”地叫了整整五年。那声甜甜的呼唤,成了我童年背景音里最得意的乐章,从未有人怀疑过这“姐妹”关系的根基。
直到那个改变一切的傍晚。妈妈邀请了小莹来家里吃饭。饭桌上气氛温馨,妈妈随口问道:“宝宝(她对小莹的爱称),你生日是什么时候呀?”我正啃着鸡翅,闻言立刻咽下食物,抢着回答,语气里满是五年来的自豪:“妈,她属羊,四月的!我比她大五个月呢!我是姐姐!”说完,我还冲小莹眨了眨眼。妈妈夹菜的手顿住了,她转过头,用一种混合着惊讶和好笑的眼神看着我:“等等,姑娘,你刚说你比她大五个月?你九月,她四月,你怎么算的?”“九比四大呀!”我理直气壮。
饭桌上出现了短暂的寂静。随即,妈妈爆发出一阵抑制不住的大笑,笑得眼角都沁出了泪花。爸爸也反应过来,跟着摇头失笑。小莹看着大人们,又看看一脸懵的我,似乎也隐约明白了什么,抿着嘴偷笑。
我的脸“唰”地一下,从额头红到了脖子根。所有的逻辑在妈妈的笑声里轰然倒塌。数学课上那个被我嫌弃的“比较大小”,此刻像一道迟来的闪电,劈开了我五年的认知迷雾——月份,是从一月开始数的!四月,当然在九月前面!
“所以……所以……”我声音小得像蚊子哼,恨不能钻到桌子底下,“我其实……是妹妹?”“傻丫头,你可不是比宝宝小嘛!”妈妈擦着笑出的眼泪,给出了最终裁决。
那一刻,五年来所有以“姐姐”自居的画面——那些“仗义”的保护、那些“懂事”的谦让、那些暗暗的得意——全部倒带重播,每一帧都打上了“滑稽”的标签。我僵在椅子上,不敢看小莹,只觉得耳朵嗡嗡作响,脸颊烫得能煎鸡蛋。原来,我竟在一个最基础的常识上,闹了一个长达五年的、天大的笑话。
后来,我和小莹依然是最好的朋友,这个插曲成了我们之间最经典的玩笑。它让我懂得,童年最珍贵的,或许不是永远正确的认知,而是那份在误会中也依然闪闪发光的、毫无保留的真诚与友爱。那份尴尬,早已在时光里发酵,变成了一颗回味无穷的、名为“纯真”的糖。
(指导教师:韦汉琳)
评论列表 共有 0 条评论
最新导读

热门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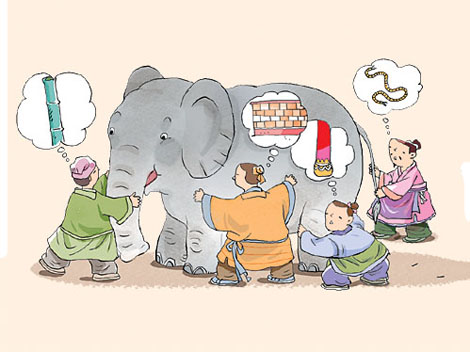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